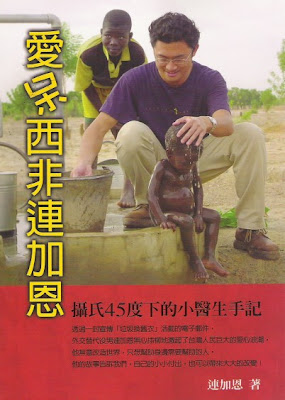一九七六年,當我有機會為亞利桑那州、土桑市(Tucson)一個地方性的報紙利用午餐時間訪問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時,整個餐廳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他來。他來這個小城是為了宣傳新片Stay Hungry--一部賣座奇差的電影。我當時是一個體育專欄作家,而當天的任務是花一整天的時間、一對一與阿諾相處以便寫下他的人物專訪。
我自己本身對他的過去也一無所知,更別提能夠預見他未來的發展,我之所以答應要採訪他完全是業務要求,而那場專訪卻讓我終身難忘。
午飯後我拿出記者筆記本,訪談中某個時刻我不經意問到:「既然你現在從健美比賽中退休了,你下一步打算做什麼?」
他以一種最沉穩又理所當然的口吻回答:
「我要成為全好萊塢第一名的票房巨星。」 對於他的計畫我試著不露出我的訝異和笑意,畢竟他的第一部作品就不被看好,而他的奧地利腔口音和笨拙又巨大的體型都不足以立刻贏得觀眾的青睞。我終於平靜下來,繼續問到他打算「如何」成為好萊塢的一線巨星。
在此得提醒您,說這段話的可不是瘦身後像個有氧運動教練的阿諾,當時的他渾身肌肉隆起又巨大,為了個人的人身安全,我試著想用最禮貌的語句去瞭解他目標背後的邏輯。
「就像我在健美比賽時用的步驟,」他解釋,
「你所要做的是創造一個你想要變成的『願景』,然後活出那個樣式,彷彿你已經是那個模樣了。」 這聽起來真是荒謬地簡單,但我還是寫了下來,而我也一直沒忘。
這些年來我一直用阿諾的概念--「創造一個願景」來作為激勵的工具。請注意他說的是「創造一個願景」,而非等待一個願景,由你來創造。換句話說,根本不需要受制於眼前的景況。
自我創造的第一步就是每天早上有某件事是一起床就想去做的--某件在你生命中急於完成的事。這個願景應該立刻被創造,而不是稍後。如果你想要的話,你總是可以改變這願景,但千萬不能片刻沒有它。一旦有了一個願景後,你就會看到它對自我激勵的力量,阿諾後來還娶了甘迺迪家族的女兒,並且當上了加州州長。
(這些標籤為「自我激勵」的文章譯自於手邊蠻有看頭的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