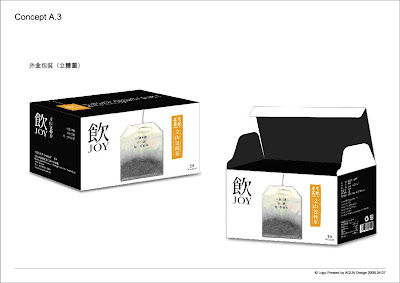村尾的圓環:種滿了印度橡膠樹、榕樹、龍柏、桑樹、樟樹、七里香、孔雀椰子...,you name it.
圓環正中央的大榕樹,三環同心圓的路面上,還可以看到健康步道。
永遠都會有來這兒採桑葉的小學生或小學生的父母(這棵是桑樹)。真搞不懂國小自然科老師為什麼會認為養蠶這個單元有什麼雋永的意義?歷30年而不改?
騎腳踏車也是童年共同的回憶,可能是因為這麼大塊空地,如果不拿來練車的話,實在太暴殄天物了,而且學會騎車之後,移動速度頓時增加好幾倍,很少有小孩忍得住這種誘惑的。在通往41弄旁邊的籃球場,出現經典的畫面:「眷村裡騎車的男孩」,他應該是某家的第三代了。
很體貼又有教養的兩個男孩。看到我在拍照,刻意低下身子,結果留下這個有趣的畫面。
41弄旁邊的花草園,是毛媽媽的傑作,這時候花開得正香的呢!
酷吧!據說右邊那種花叫做醉蝶。
41弄底籃球場旁最大的一棵印度橡膠樹,就種在環村步道旁。曾經「擾人清夢」的籃球場也早改做停車場了,小時候二姨父還跟他同事來這兒打過球呢!
從安邦街側門進來,往左手邊看過去就是步道的盡頭。
每天早晨跟黃昏,超多村內、村外的長輩會來這兒走上好幾圈。(左邊那棵刺桐被鋸掉了,後面有下文。)
沿著步道走一圈,應該有3、400公尺。
這兒竟然種了一排芭蕉。
走累了還有石椅可以休息,右邊那棵是村子裡常見的樟樹。
像這麼大叢的竹林就有四叢,品種、樣式各不同。